(希望我不会唠唠叨叨写太多的东西,也许 10000 字以内最好了.)
(最后写了 14000,就这样吧.)
出发 ¶
我出生以前,爸爸妈妈暂时住在爷爷奶奶家,我一出生,他们就决定带着我搬出去住. 开始时,我们租了一间小小的屋子,一年后他们找到了一处房子,我们搬了过去. 妈妈辞掉工作,开始专心照顾我,我们在那个地方居住了 6 年. 我 7 岁时再次搬家并转学,然后就一直没再搬动过. 我如今 23 岁,离开我童年居住的地方已经 16 年了. 最近,我开始常常做梦梦到那个我童年居住的地方,它令我着迷. 今天是清明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春光正好,我实在按捺不住,就决定回去看看.
那个地方在北京市 AA 区 BB 镇,在 CC 立交桥的桥下有一条路,顺着那条路一直走就能走到我曾经的家,地址是 X 园路 114 号. 不过在找出[我一年级时按老师要求制作的人生第一份简历(下图)]之前,我都还以为那是 116 号. 我目前居住的地方离那里挺远,骑车要骑一个多小时. 我好久没锻炼了,怕自己体力不够,就坐了公交车.

现在的北京郊区的公交车也都是很规范的了,由公交公司统一运营,每一条线路的站点设置、发车时间、行车路线都是统一规划好的,而我记忆中 16 年以前北京市 AA 区的公交车则不是这样. 那时候的公交被我们称为“小公共”,车型很小,是那种小巴车,没有固定的停靠站点,在购物商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车还会在那里熄火停上个十多分钟,售票员下车多招揽些乘客. 不同的线路依然以不同的数字作出区分,想乘车的话就在路边挥一挥手,要下车了就跟售票员说在前面路口停一下,或者跟司机说,“过了红绿灯您给我踩一脚”,意思就是踩一脚刹车. 即使路线都是固定的,在细节上还是有商量的余地,比如前面的路可以走立交桥也可以不走时,就问问乘客有没有要在桥下下车的,如果没有就选择上桥,这样就会快一些. 当然大多数时候也都不问,因为售票员的记忆力特别好,买票的时候只要告诉他在哪里下车,他就一直不会忘记.
当然售票员也有记错的时候——比如我家住的地方就在 CC 立交桥下面的一条路上,上桥的地方和下桥的地方都离那条路太远,只要是我乘坐的小公共都是一定不会走 CC 立交桥的. 然而我上学前班的某一个冬天,爸爸到学校接我,我们就乘坐小公共回家,上车前和售票员说了我们要在哪里下车,可是那个售票员就给忘了,径直上了 CC 立交桥. 我那时还小还不太认路,而且刚上学前班也才两个月,对那条路也不太熟悉,爸爸可能也只认识家附近的路,所以坐过站了好远好远. 我发觉在车上的时间比平时长太多了才提醒爸爸,爸爸赶紧去问售票员有没有到 CC 立交桥,售票员说 CC 立交桥早就过去了. 爸爸就去对线他,不是上车时说了在哪里下车的么,售票员就辩解,说他上桥之前问过了有没有在桥下下车的,还指责我爸爸说他自己不会看着点路. 我那个时候是很怕事的,受了委屈也不敢争取自己的权益,就赶紧拉着爸爸下了车,我说,“没事,咱们走回去.”
爸爸每次接送我上下学都只带 1 块钱,1 块钱就正好是坐小公共从学校到我们家的价钱. 我当时想的是,我们坐过已经那么久了,肯定已经不止 1 块钱了,赶紧下车吧,别到最后人家还要收我们更多的钱. 那时的我从来没想到过,其实这个差错是售票员的责任,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票钱要回来,坐反方向的车回家. 这就意味着下了车后的我们身无分文,真的只有走回家这一种选择了. 那天我拉着爸爸的手,就那么硬生生走回了家.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天,下车时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走着走着,路灯就全都亮了起来. 我不会忘记我拉着爸爸走上一座立交桥(另一座立交桥,不是我家附近的那座 CC,真的过站太远太远了),桥下马路的路灯就在我的身边发出黄色的光,月亮高悬. 回到家时已经晚上九点了,妈妈等我们等得心急如焚. 那个时候手机还不流行,3G 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没法及时传递消息让任何意外的事情都成了对亲人的折磨. 那一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家”的含义,那就是无论多晚、多远、多艰辛,我们总是要回家,家里有人在等待.
到达 ¶
今天的出行十分顺利,下了车,穿过 CC 立交桥下面的桥洞,就到了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我走在那条路上,感觉有点奇怪,我对那里好像非常熟悉,又觉得有点陌生. 那条路基本没有做过布局上的改动,一切都好像还是原来的样子,但[处处挂着横幅提醒大家戴口罩、少聚集、防范新冠肺炎病毒]又提醒我这真的不是从前了. 其实 17 年前的非典我正是在那里度过的,那时我 6 岁,刚上完了一学期的学前班,第二学期的学前班就因为非典又在家里玩了一年. 我对非典的印象寥寥,因为对我来说非典的那一年和我 4-5 岁在那里的那两年没有任何不同. 是的,虽然我 1 岁搬到那里,7 岁搬走,按理说是度过了六年,但我对我人生最早的记忆就是 4 岁左右,那是在一间屋子里和爸爸妈妈一起看电视的场景,好像是《别和陌生人说话》,有一个家暴场景把我当场吓哭,吓得我晚上不敢睡觉,非要和我妈妈一起睡. 于是后来我爸爸把床搬到另一个屋子里自己睡了. 那之前的任何事我都想不起来了,我不知道自己曾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租住过一年,我好像就是降生在 X 园路 114 号,我的一切童年记忆都是有关那里的,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我爱那里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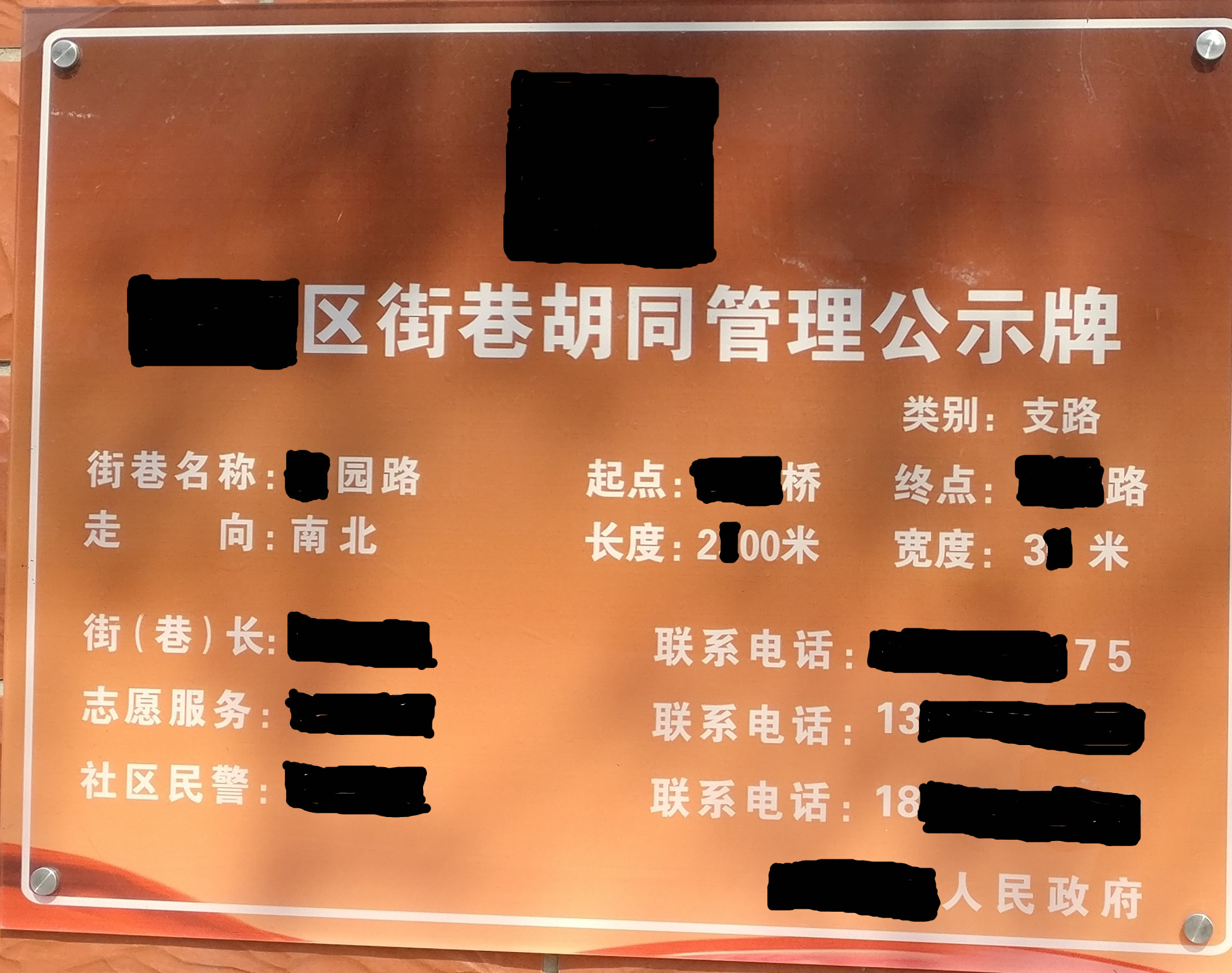
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走,看到 X 园路 112 号的路牌时我突然紧张起来——连门牌的数字都没有换过. 我赶紧掏出手机在地图上查,那个我熟悉的地方在地图上却没有任何显示,就好象它不曾存在. 我慌张极了,快步走了几步,映入眼帘的是那个完整的家——它一点都没变过,就好像我不曾离开.

门口还是曾经那个门口,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一个有生命的门口,它圆滚滚的,有点胖,无论刮风下雨就立在那里等你回家. 左右两边有两个四分之一圆柱的传达室,中间夹着巨大的铁门,铁门上有一个小门供人进出. 门上的房顶、甚至连瓦片都没有变过,下雨的时候保护着大铁门不被淋湿. 右边的传达室从来没有人使用过,我居住的时候也没有那个传达室的钥匙,它现在的样子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同样的旧护栏、同样的深色的玻璃窗,甚至连里面有什么都不知道,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承载那块门牌,那块“X 园路 114 号”. 门牌还是在原来的位置,门牌上的标识也从未变过. 大门依然是那个大门,只是被重新漆成了黑色——原来是绿色的. 左边的传达室发生了变化,它曾经是深色的玻璃窗,没有护栏——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某个亲戚来我家看望我们,拍了半天门也没有人应,就从左边的传达室翻了进去——那天传达室的窗子好像刚好忘了锁. 左边的传达室里面曾经有把椅子、有张桌子,我曾经一个上午待在那里面. 那是一个早晨,爸爸上班去了,妈妈说她要出一趟门,一会儿就回来,让我自己玩. 可是过了很久很久,妈妈也没有回来,我就跑到那个传达室里等妈妈. 我百无聊赖地翻动那屋子里所有我能翻动的东西——都是一些没用的纸张、文件,怀疑着我妈妈再也不要我了. 我就那么等啊等啊,等到中午,妈妈才回来. 她一回来我就跑上去抱住妈妈嚎啕大哭,我反复质问她,不是说好了一会儿就回来的么. 多年以后,可能是我初中的时候,我妈妈还提起过这件事,她说她当时以为我还小,小到不知道“一会儿”是多久,又怕实话实说的话我不让她出门. 她提起这件事时我正是叛逆期,当时我好像就单纯地没理她,本来这件事我也早就忘记了. 今天看到这间传达室,想起这件事,好像我妈妈对此确实有点愧疚吧.
我走上前去查看,大门被锁住了,我好像不能进去. 于是我又沿着那条路继续往前走,想看一看那条路的深处. 关于那条路的深处,我其实没什么印象的,因为我住在那里的那几年,我很少往那边去过,或者说,我爸爸妈妈很少带我往那边去过. 不过去年我在看瓦尔达的电影《拾穗者》时,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那就是妈妈曾经带我去玉米地拾过玉米. 我发微信问我妈妈当时拾玉米的玉米地在哪里,她告诉我说就在那条路往里走就是. 于是我对于那片区域的想象就变成了那条路往深处走,曾经有一大片玉米地. 此时此刻,我就身在此处,我有必要去查验一下.
拾玉米这件事我小时候妈妈给我解释过,就是有人在地里种了玉米,收割的时候却很难收割干净,于是就有一些人带着大口袋到玉米地里拾捡那些没有被收割走的玉米,这些玉米可能是不慎掉到了地上,也有可能还长在玉米植株的茎上却没被收割的人注意到,而这种行为是被玉米地的主人默许的. 对当时的我来说,我们的行动就是拯救那些被冷落的玉米朋友们,因为它们好不容易长大了,如果没有人要它们,它们是会伤心的. 这项活动听上去很有趣,而且玉米植株很高很高,在里面行走有种莫名的幸福感,行动本身当然也很有趣,我和妈妈比拼看谁能发现更多被冷落的玉米. 但玉米地很大很大,一两个小时还不能走完两趟,我很快就觉得腻了. 再加上玉米地里有好多蚊子,我很快就吵着要回家. 妈妈只好让我坐在一处,她自己去拾玉米,然后还时不时突然出现,看看我有没有乱跑,逗得我咯咯地笑. 当然拾玉米的事也就仅此一次,以后妈妈再去拾玉米就不带着我去了.
我依然记得拾玉米之后的工作:把玉米皮剥开,露出金黄色的玉米粒,然后把这些玉米堆在一起,在太阳底下曝晒. 我记得我妈妈能拾回很多很多玉米,在院子里堆一大堆,我常常为那些玉米感到高兴,觉得它们遇上了我妈妈真是天大的福分,而它们最终会被我吃掉,也算是物尽其用. 再之后妈妈会把玉米装袋,带到一个玉米加工厂,在那里能把玉米变成玉米粒、玉米面和玉米芯. 那个加工厂我妈妈也带我去过一次,但我不记得任何细节了.
我顺着马路往深处走,想象着那些玉米地现在的样子,也许它们早就荒芜了?穿过一条马路,我来到了那片应该是玉米地的地方,却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住了. 那一片地没有荒芜,没有盖上高楼,而是被改成了一片林地、花地、草地!没错了,那一望看不到边的小树和小花,绝对就是当年一两个小时还不能走完两趟的玉米地!眼下,它们正生机勃勃地成长,可见之处开满了紫色的小花. 回家后我对着《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北京分册)》仔细查了一下,这种紫色的小花叫做“诸葛菜”(Orychophragmus violaceus),十字花科,诸葛菜属,花期为 3-5 月,俗称二月蓝,“产各区平原和低山区,生于村边、路边、林缘、草丛中,常见.”

继续往前走,景色就这样一直美妙. 这个地方不算是城市,但也不是农村,也许算是个高配版的小城镇吧. 有人在草地中散步,远处有一大家子人在林地里野餐,路边有四五岁的孩子玩耍,行人道上有人正在跑步,满头大汗. 花丛里飞舞着蝴蝶——我已经好久没有追过蝴蝶了呢!曾经我家的院子里种了各种瓜果蔬菜,一到开花的时候院子里蝴蝶很多,我曾经追蝴蝶一追就是一个下午. 眼下这条公路上车辆不多,周围没有拥挤的居民区,只有马路对面有一个像是刚刚建成不久的小区. 我在林地里坐了坐,阳光斑驳,春风拂面,十分惬意,极适合读书,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岁月静好吧!那一瞬间我萌生了一个念头,我极度想要搬回来,如果那个小区有闲置的房源,这是多棒的一块地方啊.

我站起身来继续往前走,回忆起我曾经在那个大院子里的美好时光. 在我印象中,那个院子很大很大,算是个超大的四合院,爸爸说过那个院子一共是十亩地,十亩地啊,超大了!最开始是有另外一家人与我们同住的,后来他们搬走后整个院子就都是我们的了. 我们三口人也住不了那么多房间,有好多闲置的房间就是我最喜欢的探险乐园,我曾经在闲置的房间中找出大量的空白的开票的本子、和只用了一面的打印纸,我爱那些纸张,我就是在那些纸张上面学习写字,学习算术. 院子里有一棵超大的大树,我常常幻想自己爬上去玩,这棵树也承载了我后来所有文学作品中对爬树的想象——比如,我前几天才刚刚读完的《钓鱼的男孩》中就有主人公爬到书上玩的情节,这样的情节我一律是想象成我那个院子里的那棵大树. 那个院子那样好,为什么要搬走呢?
我强烈地想要进去看一看,既然大门被保留了,那里面的房子大概率还是在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居住,我曾经居住过的屋子不知里面变成了什么样. 我过了马路,掉头往回走,盘算着先从马路对面远远地观望一下,看看能从哪里翻进去. 如果前面走不通的话,我隐约记得后墙外面有棵桑椹树,妈妈有一次带着我去够桑椹吃,我们那个傍晚吃了好多好多桑椹,最后下巴都变成了紫色,还死活洗不掉,三天以后颜色才慢慢褪去. 万一那棵桑椹树还在,我也许能借助它从后墙翻进去.

这个时候,停在我家门前的两辆汽车(前面图中)已经开走了,远远望去,我家是那样不起眼,它静静地坐落在那里,任凭谁路过也不会知道那后面有什么. 哎,等等?我家左边的院墙外怎么有了那么大的一块公益宣传广告牌?!
我想起来了!我家靠近马路的那个地方其实并不是院墙,而只是一些栏杆而已,从那里是可以轻而易举地翻栏杆进入我家的!因为我记得很清楚,靠近那里的地方我们种了很多蔬菜,但有时候早晨起来到那边一看会发现那些蔬菜被人给踩烂了,到处有着深深的鞋印,这是因为那里除了有我们种的蔬菜,还有一直就长在那里的两棵香椿树,香椿树长叶子时就有人偷偷翻到我家里摘香椿. 对小时候的我来说,那些栏杆是很高的,是没法翻的,但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对于一个年轻气壮的小伙子来说,翻那些栏杆轻而易举——而 17 年后的我已经是一个年轻气壮的小伙子了,如果那块巨大的广告牌后面依然是栏杆,那我就有可能从那里翻进去!我赶忙走过去查看——

那一瞬间我有点感动,那块广告牌后面依然是栏杆,而且看上去翻过它不难. 透过栏杆往里一看,里面还是那个我熟悉的院子,那些我熟悉的房子也还都在. 唯一让我一愣的是,怎么这个院子这么小?一眼就望到了尽头?难道被拆了一半,保留了一半么?不想那么多,当务之急是翻进去看看. 但这时我有点紧张了,万一里面有人居住怎么办?万一有人看守怎么办?我定了定神,想了一下,大门是从外面锁上的,这说明即便这个院落有人居住,主人也暂时出门了;更何况这破败的景象怎么都不像是有人居住啊. 那一刻我很感谢在那里立那个广告牌的人民政府,它不仅阻挡了一些路过的人可能翻进去的可能性,保护了我曾经的家,也给我翻进去做足了掩护. 我三下五除二就翻了进去,这时我想到豆瓣有一个“佛跳墙废墟探索”小组,按照那个小组的平均水平来看,我这难度真的是零啊——没有人看管、没有摄像头监控、就在大白天光线正好的时候进入、有一个巨大的广告牌帮我做掩护、栏杆很好翻、里面的环境我很熟悉——虽然这也许算不上废墟,我翻进去也算不上探索,只能算是重温. 但我还是默默想了一下废墟探索的四个原则:不公开废墟的具体位置,不带走废墟的任何物品,不破坏废墟的原有样貌,不遗留无法降解的垃圾.
房间 ¶
虽然从栏杆外面已经看到了里面的一切,但翻过去站在里面的感觉还是突然让我无法呼吸,我反复问自己,这是不是真的,离开这个院子 16 年以后还能再次站到这里. 16 年的岁月是那样漫长,有多少楼宇在这 16 年中被夷平,又有多少楼宇在这 16 年中拔地而起;智能手机从发明到流行,北京的地铁从中心城区铺到了郊区;奥运会举办了一届、一届又一届,世界杯也踢了四年、四年、四年又四年;我搬走以后远离了自然,但我认识了数学并爱上了数学;我有了好多好多的兴趣爱好,也结交了好多好多要好的朋友;我顺利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上完了高中又读了大学. 外面的玉米地变成了林地,马路对面建起了新楼,可这个院子就好像没有人注意到它,一直都没有变过,除了变得荒芜——可是风依然吹过,阳光依然照射,杂草依然蔓衍,鸟儿依然停留.

我依稀还记得自己居住过的房间的大概位置,便朝那里走去. 其实,还是有些变化的:窗户被人用水泥封死了,这说明这里无人居住,已经废弃;门都换成了新的防盗门,我居住的时候还只是木门而已. 那时木门内侧的把手上贴着“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的字样,那是我最先认识的汉字.


其实这么多年过去,突然回来,面对这么多房间,我一时不太确定哪一扇门的背后才是我熟悉的居住空间. 我只是凭着感觉走向那个地方,然后随便找了一扇门,忐忑地试着转动了一下门的把手,幸运的是,门能打开. 我往里面定睛一看,更幸运的是,那正是我曾经居住过的房间.

按照我们当时居住时对那些房间的称呼,进门的那个就叫做客厅,里面一间稍微小一点的叫做小屋,而最里面最大的那间叫做大屋. 小屋和大屋都有单独的门,但我们居住时把它们都锁死了,一律从客厅的门进入. 这是因为我们三个人住那么大的一个院子,院墙的栏杆也不是很难翻,爸爸觉得如果所有的门有可以使用的话太不安全(那时用的都是木门),所以只留了一个门. 晚上睡觉时要把客厅的门层层上锁,再抵上与地面摩擦力很大的楔形木板,以防有人进入. 同时,客厅连接小屋的门也会在里面锁好,算是第二道关卡. 客厅里什么都不放,没有任何家具或财物,也是避免被人偷去. 实际上,我居住的那六年中,并没有发生任何偷盗的事件,只有永远也灭不完的老鼠会在夜深人静时在我家活动. 我的生肖就是老鼠,所以我小时候并不觉得老鼠是可怕的动物,我还记得有一天早上起床后,我们在客厅里发现了一只误食老鼠药死亡的大老鼠,妈妈吓得不敢碰它,是我提着老鼠的尾巴把它拿到了屋外,然后妈妈找了块土地挖了个大坑,我又提着老鼠尾巴把它放进了坑里. 我那时身高还不高,手也很小,那大老鼠比我的手还大. 多年以后妈妈在描述那件事时总是说那老鼠提起来有我身高一半那么长,我记不清细节,觉得是她过分夸张了.
客厅的尽头,对着连接小屋的门,有一间浴室. 但我小的时候从没有使用过它洗澡,我的洗澡方式是使用一个巨大的红色的澡盆. 在我上学之前,每一天的下午,吃过晚饭,妈妈都会帮我用那个大澡盆接一盆的洗澡水,放在客厅的里,往里面滴上两滴花露水. 我洗澡的时候,妈妈会拿出一本《初中生必背古诗 70 首》,是那个棕色封面的薄薄的小册子,抽查我之前背诵过的古诗. 洗完澡后,妈妈会翻开一首新的古诗,把大概意思给我讲一下,然后我们就拿着那本书一起出门散步. 我们一边散步,一边逐句地背诵那首新的古诗,我们从我家一直往北走,走到快到 CC 立交桥那里,那个地方有一个新建成不久的大圆盘,几个立着的不同颜色的巨型圆柱在头顶上方交织成一个不对称的抽象的形状. 我后来在高中的时候,班主任老师让我们介绍自己来自的区县,在那一刻,我想到的就是这座大圆盘. 小时候我们在大圆盘那里停留,我们会在那里小坐一会儿,和其他人聊聊天——那条路上有一个小区,小区好像是某个学校的家属院,住着很多退休的老教师,那些老教师就很喜欢在吃完饭后散散步——我们就是和那些老教师们聊聊天,妈妈还和其中一些老教师交了朋友,我那本《初中生必背古诗 70 首》就是某位老教师奶奶送给我的. 几个月后,我就把那整本书的古诗都背下来了,那时我才 4 岁. 那也是我第一次,和妈妈一起,提前计划好干一件事后,持之以恒地每天都坚持去做那件事,那大概奠定了我如今可以坚持做一件事的能力. 我还记得小学二年级或三年级的时候,刚一开学,班主任老师让我们准备一个周记本,要求我们每周写一篇周记. 开始时,每个周五老师都会留写周记的作业,可是突然有一个周五,老师就没有留周记作业,再然后就一直都没留过. 学期结束后妈妈翻看着我只用了几页纸的周记本,说起了我小时候背古诗的事,她说,你们班主任在周记这件事情上做得不对,计划好的事情没有坚持下来. 她告诉我,坚持是一个很难得的好品质,但像我们班主任老师那样做不到坚持的人特别多,然后她就提起了小时候背古诗的事情. 妈妈说当时我们坚持每天背古诗,最终把那本书背完就是一个很成功的榜样,我以后计划做任何事情都要记得小时候背的古诗,如果觉得自己不能坚持的事就不要计划它——这确确实实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每当我决定好好背单词,每当我决定接下来一个星期好好学习不玩手机,我都会想到背古诗的事,我大多数情况下也总是能坚持下来,这种坚持对我确实很有帮助.

我往前走,看到了浴室墙外的灯的开关,我一下子想起了小时候不知道是 3 岁还是 4 岁时做过的一件事. 那个底座上其实有两个开关,一个负责浴室的灯,一个则负责走廊的灯. 在一个上午,我好像不知怎么的不小心碰到了走廊灯的开关,走廊灯就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亮了起来. 我好像是知道要节约用电,就又把它关上了. 这时,一个奇怪的念头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中——有没有可能刚刚那一秒是走廊灯寿命的最后一秒呢?
我小时候是知道灯泡有寿命这件事情的. 理论上,爸爸或者妈妈给我讲过爱迪生的故事,爱迪生勤勤恳恳地做实验,终于找到了一种材料,能让灯亮的时间最长,所以我知道任何一个灯泡都有一个寿命,寿命到了以后它就再也不亮了;实践上,我经历过一次在晚上灯泡突然灭了,妈妈一边安慰我让我不用害怕,爸爸一边找出一个新的灯泡换了上去,屋子里又重新亮了起来,然后他们就解释到,是灯泡的寿命到了,所以它就灭了,只要再换一个就好了. 那天我就突然想到,有没有可能被我不小心碰开的走廊灯亮完了它寿命的最后一秒呢?办法只有一个,再打开灯检验一下,于是,我怀着神圣的心情拨动了开关——“啪”,走廊灯又亮了. 我满意地把灯关上,这时我想到的却是:有没有可能我刚刚检验它的那一秒是走廊灯寿命的最后一秒呢?还是只能检验一下……我于是走上了思维的死循环. 那一个上午,可能有三四个小时吧,我什么也没做,就在浴室的门口,一下一下地开关着走廊灯,打开又关上,关上又打开,直到我听见妈妈在厨房里喊我吃饭,我才强迫自己不要再去想这件事,赶紧把灯关上去吃了饭. 这件事从此就被我尘封在了记忆里,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过,直到 2020 年的今天我旧地重游,睹物思情,我才又突然想起了这件小事. 用今天的视角来看,我小时候的举动就是所谓的“套娃”啊,一层一层,直至深渊,看来我也是老“千层饼”了. 想到这件事,我实在没有忍住,“啪”地再一次拨动了那个开关——没有任何反应——那个房间肯定早就没有电了.
因为房间没有电,窗户又被人又水泥封死了,我进到小屋中只能打开手机的闪光灯,并慢慢用眼睛适应黑暗. 小屋有两张床,一张双人床本来是给爸爸妈妈用的,另一张单人床是给其他宾客用的,但因为有一次我看到电视中的家暴环节害怕得不敢睡觉,就跑到小屋要和爸爸妈妈一起睡,结果爸爸就搬到本来我自己睡的大屋去睡那张单人床了,我和妈妈就睡小屋的双人床. 后来我不再害怕后就睡小屋的单人床,妈妈一个人睡双人床,总之小屋成了我的屋子,而大屋成了爸爸的屋子.
我对小屋的记忆不是很多,唯一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是一天起床后,打开窗帘,发现窗户上结满了窗花,透过窗户往外望去,外面白茫茫的一片——下雪了. 然后我到外面去踩雪,发现院子里已经有爸爸的脚印通往外面了. 那次下雪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关于雪的记忆,它开始于小屋的窗前.

而关于大屋的记忆就太多了. 我家大屋的布局好像常常更换,我在电视上看到家暴情节的时候电视是摆在窗前的,那时我可能才三岁;而上面画的那张示意图中电视的摆放位置是我上学的时候了,因为我还记得放学回家后我会看少儿频道的一个节目叫《七色光》(经查,《七色光》是北京卡酷卫视的节目). 对那档节目的唯一的记忆是一个学英语的环节,讲了一个中国的学生到美国交换,住在借住家庭里,有一天借住家庭的妈妈给那位孩子做了一些炸洋葱圈,非常好吃,吃完后妈妈问那个孩子是不是不够吃,孩子想说够吃了,就回答了“no”,意思是“不是”不够吃,结果妈妈以为是不够吃,就又炸了一些,然后又问他是不是不够吃,他又回答了“no”,结果那一天那位妈妈给那个孩子做了好多好多好多炸洋葱圈,那个孩子也不好意思不吃,最后吃得都快吐了. 这时候主持人就跳出来给我们讲,英语里的“yes”和“no”都是对问题的直接回应,而没有双重否定之类的情况,但当时我的理解能力不过关,以为英语的“是”和“否”和中文是反着的,想说“是”的时候就回答“no”,想说“否”的时候就回答“yes”,这直到我小学二年级(已经搬家并转学走了)的时候才搞明白那个电视节目说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吃炸洋葱圈都快吃吐了这件事,对小时候的我来说是一件特别特别好玩的事情,好玩到足以把它记到今天.
对大屋印象最深的东西就是摆放在窗前的书桌,它特别特别大,我曾经在那张书桌上学习认字,在那张书桌上学习算术. 我小时候特别笨,十以内的加减法学了一下午还没学明白是怎么回事,气得在旁边旁观我妈妈教我的爸爸上来就打了我一耳光,我伤心地哭了. 从那以后妈妈就不让爸爸教我东西或者旁观我学习了,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特别特别害怕我的爸爸,直到现在我也不会主动找我爸爸说话. 关于那张书桌的另一个记忆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夏日的下午,我看到一只蜘蛛在窗户外面艰难地对抗狂风和暴雨,我就爬到书桌上面,跪在桌子上,用脸贴着玻璃观察那只蜘蛛.
也许炉火的事情会是读者们比较好奇的,其实就是我家的暖气不够热,就自己买了一个炉子,搭了烟囱,冬天到来的时候,就 24 小时不间断地一直烧,直到冬天过去才熄灭,就好像是奥运的圣火. 烧的东西叫做蜂窝煤,就是圆柱的黑色煤块,上面打着一些圆柱形的洞,炉子里大概可以放 3 块左右,下面的最接近火源,最先被烧完,然后就用钩子从炉子下面的小窗口把烧完的煤块钩出来,再用夹子夹一块新的从上面放进去,一块煤好像能烧一天?炉子除了有取暖的作用,在上面也可以烧开水,非常方便. 蜂窝煤冬天之前要从街上拦下一辆拉着煤块四处售卖的拖拉机,引着拖拉机开到我家院子里,把煤块卸到某个角落;同样是从大街上拦下拖拉机卸货购买的还有冬天前的白菜. 我妈妈后来说过在我 2 岁的时候有一次对那个炉子产生了兴趣,我妈妈告诉我说那个不能摸,太烫,可我还是等我妈妈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用手去摸那个炉子,手上起了好大一个水泡,我当时就哭了. 但这件事我完全没有印象,3 岁之前的任何事情我都不记得,就好像 3 岁以前的我是另一个人,他在我家里生活了三年:他 1 岁时住在一个特别小的地方,又被迫搬了家,2 岁还被炉子烫了手,他可能痛恨这个世界,就跑到别的地方去玩了,走之前把那具肉体送给了我. 不过这具肉体对我来说没什么缺陷,一点都看不出手被烫过的痕迹——事实上,未来这具肉体上的所有伤害都最终愈合得完美如初. 我在这具肉体里活得非常快乐,尤其是在这个大院子里的那些年. 我从客厅离开这些房间,打算再到别的地方看一看.
院子 ¶
关好门后,我便想去曾经的厨房看一看,我对厨房的记忆只有它的位置而已,我甚至想不起来里面的布局. 我到了厨房的位置,转动门把手,却发现门被锁住了. 我感觉奇怪,把其他所有房间的门都试了一遍,发现其他任何房间的门都是锁着的. 那一瞬间,我有种后知后觉的感动,眼泪几乎流了出来——这所有的房间里,唯独通往[我曾经居住过的那些屋子]的客厅的门是没有上锁的,冥冥之中就好像是这房子为我留的一扇门,它也许知道我多年以后会再回到这里,它也许盼着我回来盼了 16 年.
我只能再转一转院子了.

这座院子是我的游乐场,我在这里认识自然. 记得有一天,我家的一位亲戚带了一大笼子鸡来我家,他把装着鸡的笼子放在了[院子中间的仓库]靠西边的窗户下,然后他就进屋与爸爸妈妈说话去了. 我对那些鸡很是好奇,就跑到笼子边去看. 哇!好多只鸡啊,足足有 10 只!我便蹲下来跟它们打招呼. 我小的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在院子里玩,因为周围没有同龄的小伙伴,离我家不远的小区里住着的都是老年人,更是没有像我这么小的孩子,所以在我不知道孤独为何物的时候我早就品尝到了孤独的滋味,而 10 只鸡——就是 10 只生命,对我来说就是 10 位能陪着我玩的好朋友,我对它们的到来欣喜若狂. 于是我就非常开心地蹲在那里,和那些鸡说着话,小孩子的想象世界很丰富的,就像《玩具总动员》里那些小孩子会和他的玩具们说话、玩角色扮演一样,我就蹲在那里和那些鸡玩起了角色扮演,我还给它们都取了名字. 玩着玩着,太阳西沉,我觉得有点口渴,打算回屋喝点水,我和那些鸡们说了道别的话,让它们不要想念我,然后我一起身,一个不注意脑袋就撞到了[仓库开着的窗户上],那真的是太疼了,疼得我眼泪都在眼里打起了转. 我坐在仓库的台阶上缓了好久,脑袋上起了一个大包.
亲戚离开后,妈妈找了些干柴之类的,铺在仓库里,然后把那些鸡拿进去,圈养在里面. 妈妈说,公鸡早上可以打鸣叫我们起床,母鸡则每天都会下蛋,我们就可以吃到自己养的鸡下的鸡蛋了!自打我那天撞了头,我便没那么喜欢鸡了,我更是不把它们当作朋友了,每天只想着要吃它们下的鸡蛋. 可是等了好久,妈妈也没从鸡窝里拿到鸡蛋. 再之后,那些鸡生病了,妈妈就往鸡食里添加磨碎了的治疗感冒的过期的药,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给人吃的药能给鸡吃么?爸爸说,感冒药可以治疗禽流感,而鸡是禽类,它们生病了,当然可以吃人的感冒药. 我当时觉得挺有道理,但现在想想总觉得不太对劲. 总之爸爸妈妈没有养鸡的经验,过了不久,那些鸡就全都死了,我们一颗鸡蛋也没吃到. 而且据我妈妈说,还有一天夜里鸡舍来了黄鼠狼,叼走了一只鸡,早上起来一看,鸡毛掉得满地都是.
比起养鸡,种植蔬菜就简单得多了,妈妈虽然养不好鸡,蔬菜却种得有模有样. 我们先到一个种子站买一些种子,然后春天洒在地里,需要架子的植物要给他们搭好架子供它们爬高,然后经常浇浇水、施施肥,到了秋天就可以收获了. 而最让我觉得有趣的是,那些植物施的肥其实都是我本人的大便. 我那个时候太小,而院子里的厕所是那种老式的坑,我进去看过一次特别深特别深,我爸爸妈妈应该也是怕我掉进去,就让我在仓库后面的土地那里方便,而那些大便就被妈妈掺进土里,最终成为了那些蔬菜的肥料. 我们种的东西可多了,在厕所的北边我们种了白菜,在仓库的东边我们种了丝瓜,丝瓜结果后我觉得不好吃,第二年在同样的位置我们又种了黄瓜. 西房的西边,也就是今天我翻进来的那个地方,还种了茄子和西红柿之类的,那里还有两棵香椿树,虽然不是我们栽的,我们却也总能吃到美味的香椿.

蔬菜种植中我的贡献很多,撒种子前挖的坑是我挖的,种子是我放的,土是我埋的,浇水我也总会参与. 院子里不是每个地方都铺设了水管,我们浇水就只能用笨办法,先拿一个桶接满水,然后放在一个小竹车里推着在院子里来回跑,用碗舀着水浇,后来我们不知道从哪里发现了一个大葫芦(难道也是我们自己种的么?),就把葫芦切开,用一半葫芦舀水. 那段日子特别美好,尤其是亲眼看着自己埋下的种子破土、发芽,夏天它们开了花吸引了好多蜜蜂和蝴蝶为它们传粉,最后结成了果实,上了餐桌,吃到我自己的肚子里,那是我第一次学到延迟满足——要充分信任所有的生命,精心呵护,慢慢等待.
走啊走,就来到了曾经的桑椹树下,我开始还想着从这边后墙翻进来的. 桑椹树一直长到了房的背后,我和妈妈有时会进到房子后面,围墙里面那仅仅能容纳一个人的宽度的狭窄的过道里面探险,那里面经常能发现好物!我们常常从那里捡拾到只用了一半的粉笔,有一次还捡到了一块黑板. 我不记得妈妈或爸爸是怎么告诉我的了,但按我的理解,我们家隔壁有一所大学,大学就是一种学校,是非常厉害的学校,我长大以后也要上大学. 当然我再长大一点点要先上小学,而小学就是没有那么厉害的学校. 但无论是什么学校,老师讲课都会用到黑板和粉笔,我家隔壁的大学使用黑板和粉笔非常不节约,都没怎用完就不要了,他们不要的东西就会隔着院墙扔到我们家里来.

我们捡到黑板的那天,妈妈非常高兴,我终于不用拿着粉笔往地上写字或画画了!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在地上写字画画的,那么大的院子永远都写不完、画不完,如果连续很多天没有下雨的时候你来到我们家看,会发现院子里到处都是我的作品,当然了天一下雨这些东西就全没了. 妈妈把黑板钉在了仓库的西边墙上,为了模拟老师和学生上课的场景,妈妈又找来一张大桌子,又自己用木材和钉子做了一个特别长的长条椅子. 妈妈说她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好多人一起坐那么一个长条椅子,她还说我将来上学的话椅子就都是每人一把的了.
于是我们就开始了模拟老师和学生,我那个时候已经掌握了十以内的加减法,妈妈就开始给我讲一百以内的加减法,为了模拟出数学课和语文课,我们还制定了一个课程表,先学一会儿算术,再学一会儿识字,为了加上一节体育课,妈妈又做了一个篮球框,钉在黑板的旁边,而体育课就是我需要把我经常玩的皮球准确地投到篮筐里. 我记忆中的那个场景是在夏天,太阳懒洋洋地挂在天上,但我们在树荫下,因为仓库的西边有好大一棵大树,就是那棵我常常幻想自己爬上去的大树,就是那棵承载了我所有文学作品中有关大树描写的想象的那棵大树. 那棵大树上有好多小鸟的巢穴,我在那里上课时,小鸟就在上面一直叫个不停. 在大自然里假装上课的感觉是那样的惬意和舒适,只是 16 年后的我在想到那些场景,写下这些文字时却替小小的自己感到孤独——是啊,偌大的课堂只有妈妈一个老师,而在这个学校上学的只有我一个学生,我一个人用着那些用不完的粉笔,那条能坐下十个人的长长的长条椅子上只坐着我一个人. 我怕是再写下去就要哭了,这个段落就到此为止吧. 今天的我特意仔细看了看那棵曾经的大树,它被人砍断,显得渺小了许多.

离别 ¶
这座院子根本没有变化过,它还是那样,但为什么我觉得它小了很多呢?我打开手机,查了一下 10 亩地到底是多大,网络上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6666.7 平方米. 我估计了一下,这座院子可能长有 100 米,宽有 70 米,算下来还真是 10 亩地,而且这么看来它真的很大很大. 只是我长大了,也长高了,我见过更远的距离,我体会过更大更繁华的世界,我学习过那深不可测的宇宙,这个小院子再也装不下我了. 可无论如何,它装下了我的整个童年,我的整个童年就像梦一般,被这个院子轻而易举地包裹住了.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某一天,爸爸告诉我说我们要搬家了,我那时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该有什么情绪,我想到的是我会离开我一年级的老师和同学们,我再也见不到我总是偷偷看的那个女孩,但往好了说,也许我会有一些小伙伴可以在放学以后继续一起玩了. 搬家的时候我暂时居住在奶奶家,等爸爸妈妈收拾好一切,把新房子也装修好后,他们从奶奶家接上我,直奔了新家. 我从来没有正式告别过这座院子,对这座院子来说,我就像是不辞而别,而这一别就是 16 年. 今天我决定好好和它告别,毕竟它为我还留了门. 我再次环顾四周,深深忘了它一眼,然后轻声说了句“再见”.
翻出去的时候,我想起当时我和妈妈种蔬菜,我们还在院子中所有水泥地被破坏裸露出泥土的地方撒上过红豆的种子,那些种子我们一年没有打理,但凭着它顽强的生命力,到了秋天它还是结出了果实. 那些红豆植株的茎和叶在秋天时变得坚硬而且很脆,只要轻轻弯折它们,它们的豆荚就会爆开,一颗颗红豆洒落一地. 我用小小的手把那些红豆一颗一颗捡拾起来,那时的我虽然背过带有红豆的古诗,却不知道红豆代表了相思.

CC 立交桥附近的那个大圆盘,那个好几个圆柱体组成抽象形状的大圆盘,那个我高中时还想起过一次的大圆盘,已经不在了. 但 CC 立交桥附近有一条铁路,还是原来的模样,我小时候常常沿着它走. 我又沿着这条铁路走了一会儿,才回到大路上,坐上了回家的地铁.